古有愚公移山,今有大发凿渠!他花了36年绝壁开“天渠”!彻底改变了一个村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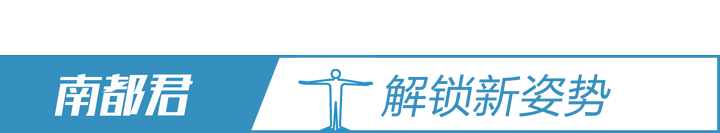
1995年,身处贵州大山腹地的草王坝村,迎来命运的转折———绝壁之上,一条天河般的水渠倾泻而下,生命之水终于流入草王坝。

嵌在半山腰中的大发渠。

这条天河般的水渠,历经36年的波折,凭借人力,硬生生地绕过三重大山,接通草王坝与水源地,村民叫它“大发渠”。大发,取自村中老人黄大发的名字。
村民说,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如果没有修好水渠,草王坝村或许已消失在近年易地搬迁扶贫的进程中———不可否认的是,黄大发与草王坝村,创造了另一种闪耀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光彩的中国式奇迹。

82岁的黄大发仍坚持着巡渠的习惯。
---失败---
草王坝村,深处贵州省遵义市大山腹地。
没有什么词比“山高水远”更适合描述它。最高的山海拔1400米,最低的600米。西面的螺蛳水河,距村子不过六公里,但一层层屏障,将水源生生隔开。面对巍巍群山,人们穷得无可奈何。
直到1992年,村民仍然不知道白米饭的滋味。因为缺水,他们只能在干裂的土地上种下玉米,年复一年喝着带着黄泥的“望天井”水,一日三餐吃着“包谷沙”———玉米粒磨碎蒸的“饭”。
黄大发,土生土长的草王坝村人。“让村里通水,让大伙能吃上大米饭”,多年的穷困凝结成这个简单朴素的想法。
1958年,黄大发23岁,出任草王坝村大队长。当了“官”,梦想迎来实现契机。上世纪60年代初,他第一次带领村民兴建水渠。
这一修就是十年。
没有技术人员指导,村民们用的是土办法:没有测量仪,全靠眼睛瞄;没有水泥,沟壁直接糊上黄泥。水一来,直接冲垮。屡战屡败,士气也就渐渐泄了。跟着黄大发上山干活的人越来越少,直到不了了之。
山间上的那道废渠,像黄大发心头的疤。
草王坝的日子继续穷着过。村民们依然去山下的“望天井”排队取水,一来一回两个小时。1990年遵义大旱,整整四个月几乎没有雨水,水井自然也无法“望天”。全村的包谷尽数枯死,地里一片焦黄。
“要是当年水渠修通了多好!”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有村民会这样想。一转念又觉得自己是说梦话,“试过了,就是修不通嘛。”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要想吃大米,三十晚兮(晚兮,方言,即晚上,编者注)才有米汤喝。”修渠的事,渐渐被抛到脑后。

黄大发行走在乡间小路上。
---坚持---
黄大发不愿接受贫穷的“宿命”。
1989年,时年54岁的黄大发被调到枫香区水利站学习。他大字不识几个,学着别人看工程图纸,费很大劲才搞明白啥是分洪沟。工程图一般用“+”代表增高,“-”代表降低,追着同学问才学会。
“他当时特别着急,搞明白了之后还说‘直接说高高低低不就行了嘛’,我们都笑。”多年以后,同班同学雷关刚还记得,黄大发年纪大,却最爱提问。
区里伙食好,有米饭吃。学习期间的一次聚餐,有人跟黄大发开玩笑:“是大米饭好吃,还是你们草王坝的包谷沙好吃?”
一句话,说得黄大发如鲠在喉。他讪笑着没有说话,心里却堵满了气。他气自己堂堂七尺男儿,遭到这样的当众嘲笑;他更气草王坝穷,穷得远近闻名,过不好日子还要被人看不起。
“还是要把水引到村里来。只有通了水,村里才能脱贫。”时任村支书的黄大发,有了水利方面的知识储备,再次把修建水渠提上村委的议事日程。
修渠,最大障碍不是高山绝壁,是钱。为了争取资金,黄大发一次次往县里跑。50多公里的路程,他拿不出钱坐车,一路靠双脚跋涉。但当年的南白县(今遵义市播州区),同样面临着财政困难的窘境,这使得政府对草王坝的支持“有心无力”。黄大发到处找领导,一点点磨。有年冬天,他到县水利局没找到人,干脆一路打听到副局长家等着。副局长回到家时,见到的是脸色发青的黄大发——— 在门口站了几个小时,冻坏了。
1991年,黄大发终于给村里带回来好消息:县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付6万元现金。因为无法拿出更多的钱,另外拨付38万斤玉米折抵为工程款。水利局也会派技术人员过去,不过,水利局要村里留1万元的押金。
1万元钱,全村900多人,人均10多元,有的一家就得出80多元。那时候,草王坝村的人均年产值才80元。“70%支持,20%犹豫,10%反对”,村民徐国太清楚记得,村里的人心并不齐,“第一次修渠失败了嘛,有些人没信心。”
黄大发家家户户地劝。家里有鸡有猪的,卖了换钱。实在拿不出来的,借钱也要交上。钱终于凑齐了,但难免有人交得不情不愿。
“黄支书受的委屈多了。”徐国太说,那之后,黄大发的家里就屡次遭到破坏。杜仲树的树皮被刮掉,过冬草被烧,猪被偷。但徐国太没见过黄大发生气。他抓到偷猪的人送去派出所,黄大发对他说:“我知道是谁就行了,你们别打他。”
---开山---
1992年春,水渠正式动工。
所有人都要投工投劳,领了钢钎、铁锤等各种工具,每天去工地上班。300多吨水泥,黄大发亲自从160多里远的龙坑一车一车运回草王坝,村民们再一袋一袋地背到山上的工地去。

当年,黄大发也是这样子,带着村民徒步去修渠。
困难四面八方地来。修渠要经过邻村土地,放炮的山石掉下去,砸到别人家的房子或田地,又免不了起纷争。被砸的乡亲找上门来要赔偿,都是黄大发出面顶住。
其中一些人难缠,腰间别着刀上山阻挠,说要跟黄大发拼命。“没怕过。就给他们做工作嘛”,回想起来,黄大发不怒反笑。最后,乡党委书记出来为草王坝“撑腰”:砸到邻村房屋的石头,草王坝村赔;砸到地里的,就自行解决。
从水源地螺蛳水至草王坝,经过大小七个悬岩,十多条峻岭,其中以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最为险要。想开凿水渠通道,需从百丈悬崖峭壁上先打出半隧洞。
没有任何专业设施,村民们就用箩篼把人吊下去,半靠着绝壁打炮眼,两天、三天打成一个。放炮,凿岩,砌沟,和水泥灰浆。一丁点一丁点地炸开岩石,水渠一尺一尺、一米一米地延伸。

村民们在擦耳岩段用钢钎凿开岩石,当年就是靠着这些简单的工具,他们得以在峭壁开出一条水渠。
悬崖上修渠道,黄大发担心出事,便把一些施工段包给了村外的专业工程队。在转拐岩,山体像刀削般直立,工程队也怕了,没人愿意下去打炮眼。徐国太急了,被黄大发拦住:“我来。”
“你们不要怕。我下去安全得很,没问题,没问题。”黄大发把绳子系在腰上,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悬崖边。绳子另一头系在树上,几个年轻人拖着慢慢下放。
四丈长的绳子合13米,大约半个小时才放到头。只听黄大发在底下喊:“绳子放下来,还没到!”徐国太探头下去看:黄大发把绳子系在另一棵树上,又放了四丈,才到标记的位置。
安全确认了。工程队也先后跟着下去。

黄大发叮嘱渠边行走的村民们注意安全,崖壁另一侧则是深山谷。
---通水---
在黄大发二儿子黄彬权印象中,父亲始终为村里的事情忙碌,极少过问家里。“他出门从来不打招呼的,说走就走了。”
要是到了晚饭时黄大发还没回来,黄彬权就得去家门口地势高的地方,对着群山大喊“爸爸”。山间传来回应,远方有手电筒的光点一动一动,家人就知道,黄大发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黄彬权理解父亲的梦想:“集体的事情太多了,他无法考虑家里面。”
1995年春,第二次修渠开工仅三年,7200米主干渠、2200米支渠全线通水。
黄大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哗啦哗啦的,晚上睡觉也能听见。”水声让他欢喜。
村里随即开始搞“坡改梯”,把山崖开垦成梯田。到1997年春天,全村坡改田约300亩,人均粮食增至千斤,人均产值则从80元翻至300元。
“田太多了。”村民黄兵凯发出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叹。

黄大发在田里
---修渠的老伙计们---

▼ 徐开伦

上世纪60年代,黄大发首次牵头兴建“红旗水利”,徐开伦便与黄大发并肩作战,也同样经历了红旗水利的失败。1992年,水渠重新动工,徐开伦是指挥部成员之一。水通那年的春节,村里家家户户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新米拿出来煮饭,徐开伦一口气干了五大碗。
▼ 夏时强

“大发渠”开工时,夏时强的孩子年纪都很小,放在家中无人照顾。夏时强便和妻子想了个办法:把孩子装进背篓里带到山上。两口子干活时,就在不远处铺上床单,让孩子躺在上面玩。
▼ 黄兵凯

黄兵凯清晰记得,1994年通水那天,从水源地到草王坝,水渠沿线挤满了人。村里随即开始搞“坡改梯”,把山坡开垦成梯田。“田太多了。”他感叹,家中原本的五分田增加到五六亩,以前耕田只要两三天,水渠修通后则花了两个月,终于可以栽培水稻了。
▼ 黄兵强

草王坝村所在地已属高寒山区。冬天,水渠工地上常常落满大雪,但村民们照样开工。“手冻得哟,都裂口子了。”黄兵强说。工地离家远,黄兵强会在早上炒好“包谷沙”,或是烧熟红薯带到工地上充饥。修渠三年,他吃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冷饭。渴了,就喝山沟里的水。
▼ 徐开立

1992年春,第二次修渠开工没几天,炸落的石头掉到山下,砸坏了别村几户村民的田地。他们围到工地上,不准草王坝人施工。徐开立跟着黄大发,挨家挨户赔笑脸、道歉,到田里把石头捡拾出来,几户村民还是不依不饶。“后来还是乡里的领导出面调解,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徐开立说。
▼ 黄大能

黄大能也跟黄大发一起参与了第一次修渠。他说,那时候村民们不会做规划,直接从水源地开始修,边修边引水,水流往哪里就往哪里挖沟,遇到有大石头挖不动的情况就绕行。没水泥、没技术、没经验,修了十几年也没修好。第二次能很快修成,还是因为准备充足了。黄大发去水利站学习了两年多,又带着技术人员在山里测量、规划,搞了大半年才正式动工。
▼ 唐恩良

第一次修渠时,唐恩良才十二三岁,曾跟着学校老师到工地上去慰问。十多个学生,每人从自家菜地摘了些菜,带上工地煮给大家吃。第二次修渠时,唐恩良已成了修渠的主力,经常要背着100斤的水泥上山。他说,平常干农活也累,但修渠更累,一般不会背这么重的东西,而且每天都要上工。但那时候,大家都咬紧了牙关地干,没人叫苦叫累。
---办学---
通水后,黄大发带领村民盖起了小学。
黄彬权从1997年起在村里当代课教师,待遇不高。2003年,他到县里去打工,两天的工资就抵得上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
哪知道没过多久,黄大发来县里找他了。“说村里面缺老师,让我回去。”黄彬权不想回,但更不愿为难父亲,最终还是跟黄大发回了家。2006年,因为待遇问题,他再次进城打工,又被黄大发劝回。自此,黄彬权没有再离开草王坝村。
通了水,多了田,村里的经济状况渐渐好转。有编制的正式老师也逐渐进驻。
黄彬权下岗了。年纪已大的他没有再动打工的念头,转而务农。生活自给自足,盖起了二层楼房,但也仅此而已,家里并没有更多的积蓄。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坚决不回村里,生活不会是现在这样。
不过,黄彬权从未对父亲说起过这些。“当时已经做出选择的事情,就不能怪罪别人了。”
上世纪90年代至今,村里考出了20多个大学生。“没钱,哪里供得起大学生?”有村民说得直白,“水通人发。”

黄大发在团结村小学,向学生们讲述当年修渠的故事,勉励他们好好读书,努力改变家乡的穷面貌。

学生们正认真听黄大发讲述修渠的故事。
---牵挂---
2004年,黄大发离任村支书,不再担任村干部职务。他心里始终牵挂着护渠修渠,时不时就到渠上看看。
“让村里通水、通电、通路,这就是我的梦想,我一直没有放弃。”今年,黄大发82岁了。村里的水、电、路都已修通,村民们到县城区可以坐车,不用再像他当年一样纯靠走路。
他还住在多年前盖好的木板房里。家里没什么摆设,墙纸处处洇出黄渍。多年来的工程图纸和获奖证书,包得好好的放在靠墙的麻袋里。有台彩电,是五六年前女儿出嫁后给买的。

绵延三十多年的修渠往事,在他眼里反而不值一提:“想吃大米饭,我们就要大家干。我是党员,我带头,全力以赴,敢于担当。”
去年底,乡里开始搞新农村建设,帮助村民们重新修缮房屋,政府出大头,村民自己承担一部分资金。
“一说要出钱,又有人不干了,都不愿意出钱怎么办嘛。我来出。”集体会议上,黄大发第一个举手同意。

他有更多的想法待实现。水渠让塌方砸坏了多处,得重新翻修。村里的路通了,但还有好些地方是黄泥路面、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毛路”,能都改成水泥路就好了。村民还未全部脱贫,要重视起来,帮大家增收。

黄大发心深深地扎在草王坝,勤勤恳恳地为村民服务,让这片土地生机盎然。
---现在的草王坝---

2016年底,“新农村政策”在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乡仡佬族乡开始执行。得益于“大发渠”的水源,黄大发所在的团结村350余户,1200余人免于搬迁,原地建设回迁。
戳视频↓↓
看黄大发的修渠故事
采写:南都记者 冯群星
摄影:南都记者 陈辉 陈成效

给“现代愚公”黄大发点亮大拇指 
阅读原文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