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俗气的故事丨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今年60多岁的丁勇先生是加州一所大学的教授,同时,他也是加州最有名的同志机构,华人彩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丁勇先生的母亲是上个世纪的著名女作家,何葆兰。父亲则是五四时期与鲁迅、冰心、丰子恺等同为一代的最有影响力作家之一,丁嘉树(笔名丁丁)。
1996年,丁勇先生和11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朋友在加州创建了华人彩虹协会的前身,中国彩虹协会(China’s Rainbow Association)。他们组织过华裔同志交流活动,举行过反对同性恋歧视的游行,教育并帮助那些因为同志身份而深陷挣扎的同胞们。去年,API(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 全美最大的亚太同性恋组织,为丁勇先生颁发了特别荣誉奖。
在当地报纸上经常能看见丁勇先生的身影和言论,他说,自己是个活动分子,要做出一些事儿来。“最初成立彩虹协会的时候,没有华人敢在公开场所站出来说话。我没办法,就自己站出来讲同志维权的问题。记者访问我,还管我要照片,我给的。电视台打电话说需要一个会讲广东话的同志,下午开始录制,明天就播出,问我能不能来。我说,马上就来。前年,我上电视辩论。对方上来就说,同性恋是乱伦的罪人,没有道德。

我反驳道,你拿得出证据吗?我们不看别的,就说2015年最高法院通过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时候,你没看到白宫门口挂起的彩虹灯吗?你是谁啊?你在什么时代啊?现在还是19、20世纪吗?睁开眼看看吧。”
丁勇先生的言论影响了一位华裔女性,亦凡。在报纸上看到丁勇先生的报道后,亦凡便联系了他,成为中华彩虹协会的一员。
1994年,亦凡认识了自己现在的爱人。96年,两人正式开始交往,亦凡是她爱人交往的第一个女朋友,之前均为男性。两人刚开始恋爱时,周围的邻居经常在背后对她们指手画脚。亦凡很想跟这群人理论一番,但是爱人却只是拉着她快步走过。
直到有一次,当两个人正在家里休息时,几个警察找上了门,说有人举报亦凡家里有不三不四的人做违法活动。亦凡冲上去说:“谁不三不四了?我们做什么违法活动了?”警察转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亦凡看着自己的爱人因为二人的关系不断陷入长时间的痛苦和挣扎,于是决定劝说爱人向家人坦白自己同志的身份。爱人不理解,埋怨她:“你怎么这么自私?只想着自己。”
2002年,不堪于周围的压力,亦凡的爱人提议两人出国。当时美国911事件的余波还未平息,大使馆的签证通过率很低,而亦凡最不期望的结果发生了:她过了,但爱人没过。她们没想放弃。两人又一起去了趟泰国,希望能在第三国登记结婚,但由于泰国仅限本国人登记结婚,所以仍是拒签。过了几年,亦凡建议爱人直接在签证的时候向大使馆坦白自己女同性恋的身份,爱人照做后,大使馆直接回了一句:“你们这不是摆明了要去美国移民吗?”又是拒签。

无奈之下,亦凡决定自己先到美国生活工作,拿下绿卡后再把爱人接过去。没料到,此后一别竟是长达十几年的异国恋。在这期间,亦凡找到了一份外贸公司的工作。由于业务繁忙、身份不稳定,亦凡每两年才能回国一次,和爱人相聚。平时,两人只靠电话交流,也不会用QQ或者其他网上聊天工具。亦凡的爱人甚至为了避免周围人对她的指指点点,搬到了上海工作,也变得愈加内向、沉默,仿佛隔离在了另一个世界,孤独生活。
据亦凡讲,她的爱人其实一直不太爱说话,而亦凡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与她无话不谈的人。刚交往时,亦凡的爱人很难接受两人的恋情和身份。感情爆发到极点时,爱人便哭着让亦凡离开、分手,结果亦凡没走几步,爱人马上喊到,你回来!
年轻的时候,亦凡曾想过做变性手术,她觉得自己是一个男性却装在了女性的身体里。她调查了好几年,而父母担心她手术有丧命的风险,所以百般阻挠,亦凡只得罢休,但是也让父母勉强接受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也不理会街上人对她“不男不女”的评价,亲戚催婚介绍对象时,也经常直接坦白自己的性向。她说:“我从小就是个假小子,不穿裙子,只玩男孩子的游戏,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但是我爱人不一样,她是一个很温柔、有女人味的女性。她比我面临更多的压力,周围的亲戚和朋友总是在问她为什么还不结婚生孩子。”
这样的环境使得亦凡的爱人不得不对两人的关系遮遮掩掩。在中国遇到熟人时,亦凡的爱人也从来不会公开她们的关系,往往只是糊弄一句“是朋友”,“是姐姐”便作罢。
在日夜的焦虑以及无法与心爱之人见面的情况下,2009年,亦凡的爱人选择了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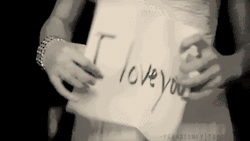
幸运的是,爱人最终在医院被抢救回来,之后便被她的家人接回老家,修身养息。很久以后,亦凡才听爱人说起这件事情,“我爱人可能从小性格上就有一些缺陷,再加上出国那几年我不在她身边,周围的亲戚还一直给她压力,让她结婚,她才会这样想不开。一直以来,我都鼓励她,安慰她,让她知道,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虽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放弃,保持这份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
从两人在26岁那年相识后开始,这段感情经历了不曾中断的非议、家人的阻挠,以及现实的无数次打磨。有人问亦凡,这样的坚持和信仰值得吗,与其经历这样长时间的痛苦,为何不直接选择放弃?亦凡说,对爱的信仰就是支撑她一个人在美国打拼的力量。
2015年,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以后,45岁的亦凡终于在6月份把爱人以未婚妻身份接到了美国。7月,两人结婚注册。注册当天,亦凡只邀请了几个朋友前去见证,吃了顿饭,告知了母亲,并没有举办婚礼。母亲祝福亦凡:“你们俩现在终于可以一起幸福地生活了。妈妈现在老了,也帮不了你们什么,只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在美国幸福。”
结婚并没有带给这两个人过多的兴奋感,亦凡说:“我们俩已经异地恋这么多年了,说实话,结婚的那种激动已经没了,因为实在太久了。包括我之前问我爱人拿到签证高兴不高兴时,她说也算开心,但是那种兴奋早已磨没了。”
现在的亦凡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爱人还在适应阶段,正在学口语。来美国以后,亦凡的爱人变化很大,她变得开朗,愿意交流,认识了其他的同性恋朋友,也一起去旅游、运动。最让亦凡惊喜的是,两人一起去看医生时,医生问她们俩什么关系。这一次,爱人回答说,“她是我的伴侣。”
我爱人拿到签证高兴不高兴时,她说也算开心,但是那种兴奋早已磨没了。”
亦凡曾接受过不少关于同志的采访,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同性恋群体。她说:“你如果想得到平等的权利、他人的理解,就要自己去努力争取,去展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能永远躲在后面,让别人看不到你,听不到你。”
就在亦凡为同性恋群体发声的同时,一名中国本科留学生Allen正和LGBTQ的同学们一起坐在学校的办公楼里静坐示威,要求校长针对Trump上台后对同志的消极态度发表意见。
Allen来自一座北方的小城市,现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所大学。十三岁时,当周围男生都开始对女生有好奇心时,Allen发现自己竟然从未对女生有过想法,反而对男生有些朦胧的感觉。那时的Allen并不敢告诉父母这件事情,他说,“刚知道自己同性恋身份的时候,我很排斥。我当时想,我肯定不会告诉我爸妈这件事情,我会找一个女生结婚,不让父母因为我感到羞愧。我还每天幻想,如果有一天早晨起来,突然发现自己不喜欢男生了,那就真的太好了。”
十六岁时,Allen离开家乡来到美国念书,然而他与父母的思念和沟通也仅限于每两三个星期的简短通话。出国前,他也曾担心过家里的经济负担,但是父母的回复只是:“你不用管,小孩子不用担心这些。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们也要让你出国。”砸锅卖铁这四个字重重地敲打着Allen的心,也让他更加害怕做让父母失望的事情,比如公开他的身份。Allen说:“我不会现在就告诉父母我是同性恋。我怕他们会断了我的学费,觉得是美国把我变成了这样。等我经济独立以后再说吧,希望不会太久。”

在美国,Allen经历着双重歧视,一方面他身为同性恋被大众歧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亚洲人,他在同志圈里被白人歧视。刚刚出柜不久时,Allen在Gay吧遇到了一个很可爱的男生,正在他准备过去搭讪时,那个男生马上抛了一句:“对不起,我不喜欢亚洲男生。”听到这句话,Allen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觉得内心被狠狠一击。他慢慢发现,学校的同性恋组织里大部分都是白人,其他族裔的人少之又少。而他自己,作为一个亚裔同性恋,在圈子里混时总感觉有些吃力。
于是,他决定站出来说说话。他成为了他们学校LGBTQ组织里,唯一一个肯公开发言的本科国际生。他开始和更多的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把和他从前一样迷茫的人解救出来。他说:“很多少数族裔的国际同性恋学生觉得种族歧视不重要,Trump的上台对他们同性恋的身份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其实不是的,只要你生活在这片国土上,你的利益一定会因为他的决策受到侵犯。而我一个人的声音太小,所以我想借助LGBTQ集体的声音,让我的声音更明显,也让更多同性恋国际生,尤其是亚裔留学生,站出来为自己维权。”
对于未来,丁勇先生、亦凡和Allen都有自己的打算。在美国生活已久并工作稳定的丁勇先生坦言自己不会再回到中国生活,Allen说自己并不一定待在美国,但打算找一个同性恋婚姻合法的国家定居,唯有亦凡表达了自己回国的意愿。她说:“在中国,每个人之间的感情联系都非常深厚,但美国没有这样的亲情。所以我想,也许老了以后,我会带着爱人回国养老,没事儿了就和从前的朋友们聚一聚、唠一唠,也挺好的。”
一直以来,人类都倾向于以群居的形式生活。在遇到文化的裂变、自然的改变时,一部分人便会选择迁移到另一个地点,开始新的生活。他们跋山涉水、漂洋过海,来到一个新的国度,遇到思想上的碰撞、情感上的化学反应,酿造出一个个“新生”。你无法通过表象判断“脱离原始地”这件事情是否对他们产生了本质上的改变,但你能看到的是,因为这样的脱离,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以及一个更加自由、勇敢的灵魂。

作者:秦之琳
美编:阮佳镱
本文收录在NEBULAR第二期杂志
点击下方图片获取更多杂志详情
▽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