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美国的第52个州


卖面的老爷爷告诉我,书里读来的,是骗人的,美国其实有52个州,50个州加上温州和福州。“他们温州人买房子,我们福州人开餐馆的呀。”
福州人花了三十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把中国搬到了一条街道上。一个生命,从襁褓婴儿到病逝老人,他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全部联系,都可以在这个街道上完成。
他们抛弃了自己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触犯法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在厨房,前台,按摩房,美甲店努力十年,最成功的结果,是再次成为一个普通人。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是不容反驳的,“再苦再累,好歹我是在美国啊。”
全文共5014个字,平均阅读时间5分钟。
我是在三月的时候乘了最快的高铁从北京南站到福州,要跑7个小时48分钟。自上车之后,周围的语言自动转换成了南方的调调。福州原来叫榕城,方言自称为“平话”,我熟悉这种语调是一次在布鲁克林的八大街吃饭时服务员讲的。
当天我和朋友赶早排队去吃早茶,餐费大概是27刀,我俩给桌子上放了3块多的零钱离开。刚出门,就被一个穿着黑制服的人从背后叫住了,他普通话很差,英语也不通,我们断断续续地听出他的意思——小费不够。
一顿饭吃了半个小时,我俩从头至尾都没见过他,这张陌生的脸强压着怒气跟我们争辩,看我俩最后也没有掏钱的意思,说出了第一句我听得懂的完整的话,“没有钱就别来这里吃啊。”扭身走了。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很想吵架但语言不通的无奈。
福州不小,我到的时候正在下雨,出租车从西北往中心开,堵在高架上。街道上每隔10米就有一家卤味店,遍地都是沙县小吃。福州种满了榕树,榕树喜温,福州四季常青。
福州还在这里。但福州人,去了美国。
美国有多少福州人?因为他们身份的不合法性,很难计算的出来。但是对于一个福州人来说,整个世界都是福州人。他们跟随福州人偷渡,被福州人接待,去福州人开的餐馆里打工,每日和福州人讨论另一个福州人的八卦。直到结婚之后,才会生下一个美国人。
李叔今年50岁,24年前用了极端的方式来到波士顿。他跟了一位蛇头(指专职帮助人们非法偷渡的人)跑到台湾,上了艘破烂的小渔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两个多月,一路向东漂过来。补给不够时,那些看起来扛不了多少天的老人便会被扔下船。得了重病没法医治的,死前就会被扔进海里,害怕尸体会引发瘟疫。“那个年代偷渡就是这样,上了船就知道可能会死在上面,但没有给自己退路。”
如今,李叔在波士顿的中餐馆里送外卖,兼职做Uber司机。在娶了一个“有身份”的女人之后,他已然当了十几年的美国人了。“我来美十五年之后才第一次回中国,家乡的人都认不出我来了,这几年生活稳定了,在他们眼里也算事业有成。”他只是轻描淡写地概括自己一半的人生——《北京人在纽约》根本就比不上自己当年的经历。“不知道害怕,那时候年轻,都把钱看得比命重。”
十几年前李叔偷渡的时候,人民币和美金的汇率是9比1。家里有一个人去美国,一个月做餐馆赚两千块钱,自己花五百,余下的寄回国,就是一万多块人民币。父母买车,盖房,还有余钱做些小生意。在街坊面前可以昂首挺胸地说,“我儿子在美国赚的。”
李叔老了,但福州的年轻人还同他当年一样。
张申凡也是福州人,08年跟着蛇头来到美国,他们一行十几人,先坐车到北京,乘飞机到墨西哥。又从墨西哥爬山,跨过边境进入德克萨斯州。还是艰难,但比起李叔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安全得多了,起码最后可以体面的,坐飞机到纽约。
“到美国去”对于当年十八岁的张申凡来说是一个没有过脑子的选择,他在美国的亲人比在福州的还要多。他兄妹三个,哥哥03年偷渡到美国之后靠结婚拿到了身份,现在有了一儿一女,都在纽约上学。姐姐在福州结了婚之后,夫妻俩一起到美国做餐饮。
他跟哥哥最亲,“每两三天都会通一次电话,有些不能和父母说的话就和我哥说。”他刚落地纽约的时候就是哥哥去接他,在确认张申凡安全之后给了蛇头五十多万的人民币。这些钱里有张申凡在上海打工攒下的六、七万。其余的坑,是他父母填的,老两口在福州做小本生意,运转的资金来源于哥哥姐姐。
日
落

我在福州的落脚处选在三坊七巷的边儿上,央视在2011年为此地拍过一个六集的纪录片,讲这里的白墙瓦屋养育了100多位光耀历史的人物,宣传时写,“福州要被全国的城市羡慕”。
福州人做灯,生动细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文物。三坊七巷的主街叫“南后街”,把老城从中隔开,东边三坊,西边七街。冰心写过这条路,“我们老家就在福州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影下人流潮涌。”
福州是座老城,年轻人对自己未来的期许,不在此。
张申凡老家是福州边上的贵安村,他十四五岁时离家去上海打工,常住南方,在到美国之前,没见过大雪。到波士顿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被福州人介绍到餐馆的后厨帮工,跟着师傅学炒菜。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张申凡对波士顿的印象不是冷,相反,是热。不管外面风雪如何凛冽,后厨的一年四季都是一个样子:围着火的,热。
中餐馆不断地扩张、复制中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流水作业下单方式。配菜、烹炒、装盘、清洁备料、外卖装盒,每个人职责明确。三个厨师里一个负责蒸,炸,冷盘,其余二人分摊所有的炒菜。张申凡进入后厨拜师学艺,每个菜放什么,配比多少都是规定好的。十年前,他站在师傅边儿上看师傅一晚上做一百多份干炒牛河;今天,他工作的餐厅已经换了几家,自己颠勺,每晚也是做一百多份干炒牛河。
每个厨师面前都有一个出单的机器,他们的工作,就是把单子上的菜炒熟。饭点的时候,出单的机器哗啦一声,单子跟流水一样,来不及扯下来,白花花的一片堆在下面。大致瞟一眼抬手,油就已经进锅了,行动必须要走在大脑前面。
再老练的师傅单子也会搞错,店里光炒饭就有牛肉,素菜,海鲜,酱油等十几种,煎饺更难分辨,馅儿包在皮里面,哪有人分得清是牛肉还是猪肉,下锅只凭多年做工的直觉。如果错了,服务员总是会先上,然后祈祷客人尝不出来。
在厨房,忙的时候,没有时间容你思考。而闲下来的时候,没人愿意思考,思考让时间过得很慢。
不在饭点的时候,张申凡会和几个伙计从灶台上撤下来,坐在几个装废料的白塑料桶上抽烟。负责清洁的是一对西班牙兄妹,哥哥安东有着传统西班牙人的性格,总是冲着店里的女服务员抛媚眼,只是他不会说中文,服务员们不会说西班牙语。他们便宜,清洁工也不需要说话。
张申凡和店里的伙计们也喜欢逗这个他们能接触到的,为数不多的外国人。厨房地方很小,每次在走道儿碰上,伙计们都排着队戳他,“嘿,安东,Fuck you!”安东一听这话就笑起来,却又佯装
愤怒地怼回去,“NO! FUCK YOU!”几个人作势就要打起来。经理听见吵闹声过来,刚搭好要干架的场子一哄而散,张申凡他们又躲到一边抽烟。
一根烟燃尽了发现经理不在,又喊起来,“嘿,安东,Fuck you!”每天如此。
张申凡做工的店位于波士顿K town,周一至周三每天都营业至凌晨两点,周围是波士顿大学生扎堆的地方,夜里生意很好。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子是在1点50分接的,他正准备收工回家,收单机就响了一下,后厨的伙计陪着他生气,“企台(服务员)这女的脑子有毛病,这么晚还接单。都叫她不要接了还接。”
转头去看企台姑娘同是一脸怨气,她在这个位子上坐了12个小时了,这个点接客人,下班时间起码要推迟半个小时,只是经理在旁边逼着她接单,不好说什么。
餐馆的员工对于时间总是期盼的,每过一天就离发工资更近一天,分针划过一圈,离下班就又近了一个小时。下班是最值得期盼的,可下班空空荡荡,一觉睡过去,是另一个上班。
波士顿打工的福州人大都住在唐人街或昆西(波士顿郊外的一个住宅区),每周休假一天,除了睡觉,就是结伴逛逛超市。“在美国,朋友都忙着打工,没空玩儿也没空聊天,来了快十年了,卡拉OK也就去过一次。”
在非法移民的打工者里,张申凡算是任性的,他心情不好时就几天不去做工,东家生气了,他就直接辞职,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民以食为天,餐饮从来都是一个好生意。他从波士顿搬到了纽约,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份工作,“中国人还是适合在纽约生活,过年的时候热闹,和国内一样,法拉盛那里我认识很多福州老家人。”
张申凡算着日子,明年他就28岁了,是自己在美国的第十年,他很少会主动想起父母,“每次和妈妈打电话,家里都会催我找媳妇儿结婚,说到后面双方就会不愉快。”
他尝试安置自己的婚姻大事,但在福州人的圈子里,男多女少,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张申凡在波士顿的一家餐馆后厨认识了一个小姑娘,俩人加了微信,他不做工的时候总是主动聊天,每天开始的第一句话总是姑娘的全名搭配一个微笑的表情。
这样持续了几个月,期间他也直接过一次,编辑了一条“我很喜欢你,用英文怎么写?”的信息发出去,对方回了他一个谷歌翻译的地址。

王潜龙在这家波士顿的餐馆干了几年企台了。他不喜欢留学生,觉得很多留学生“缺乏家教”,“你看看这群留学生给的什么小费,抠死算了。”
在中餐馆里干企台的福州人多是刚偷渡过来的底层,没有身份就意味着不享受任何政策上的保护。他们无法报税,没有底薪,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食客的小费。周内的午餐档生意最差,上周一从11点到5点只来了三桌客人,总共收了十三刀的小费。小白是店里新招的员工,按照规矩和一个老员工搭档,两人分成,新人只能拿百分之三十五,干了六个小时,赚了4块5毛5。
店里最大的股东姓张,明面上,员工喊他老板,喊倩姐老板娘,二人都是福州人。私底下他们都清楚,张老板法律上的妻子带着孩子生活在纽约,平时很少来店里走动,而倩姐不过是店里的一个服务员,待遇和普通员工相当,在店里只有她和其他员工的时候,她还是有一些威望的。指使起人来总爱提起,“我们家老张”,聊得开心了,偶尔也提及自己有店里的股份。
以前在店里打零工的小姑娘讲起倩姐,说她总喜欢穿豹纹低胸的紧身衣服,说话捏着嗓子,眉毛是向上挑的。“倩姐撒娇那是一流的,我们每天都能听她说好几遍,‘哎呀,我的外卖去哪儿了呀?’明明外卖就在她的手边儿上。”
倩姐不在店里的时候,剩下的人总是学着倩姐的样子说话。不论男女都拎着外卖,娇滴滴地,“哎呀,我的外卖去哪儿了呀?”
企台有自己的规矩,对于有些长期打铁(不给小费)的,或是自己特别讨厌的客人,会在买单的时候在账单里直接算好百分之十八的小费,行话叫“插单”。有些顾客人多,或是看得不细,就会给两份小费。
经理对员工的要求是五人以上的大单才可以“插”。倩姐是店里名义上的老板娘,只要她当班,每桌的单子她都要“插”,没人敢说她。昨晚倩姐没当班,错过了店里的好生意,两个企台每人分了200多的小费,刚上班不久的小白干得越来越好,王潜龙主动提起要给小白涨工资,按照老员工的待遇,拿小费的百分之五十。
倩姐看着下午空荡荡的桌椅,对着昨晚的账单生气,“这个小白刚来没多久,拿一半的小费不合规矩的,工作起来也挑三拣四,学生就是不一样,娇气得很。”
在唐人街,倩姐的身份是透明的,但她也见不得人。老张的儿子一旦到了波士顿,她便不能进店一步。餐馆的其余两个股东来吃饭聊天,她也只好躲在后厨,假装是找厨房的伙计聊天。
偷渡人打工,女人比男人多一种职业——小姐。波士顿最大的妓院开在唐人街,如今老张店里送外卖的亚叔叔初到美国时就是做老鸨的。他手下的小姐分为全职和兼职,全职的姑娘大多来自纽约,是一些还欠着蛇头钱的偷渡客。和性相关的钱,都是快钱,“干得好的姑娘能日入几万”。“纽约待遇太差了,不包吃不包住,不把人当人。我们波士顿不抢生意的,实行资源整合。小姐基本十天换一个东家,这样谨慎起来不容易被抓,还能给客人提供最新鲜的面孔。”亚叔叔只做中国人的生意,最好是能做熟人的生意,“外国人叫床声音太大。”除了妓院,唐人街还有专门的SM俱乐部,“Chinatown很多酒楼老板平日工作压力大,很喜欢被皮鞭抽个两下。”
对于每一个十六、七岁的偷渡客来说,他们的生活早就游离在教育和法律之外了。在唐人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留了着古老中国社会的影子,无所不知但又秘而不宣。每个人都生活在别人的嘴里,流言和八卦是行为的约束。
夜里两点一过,K town唯一一家营业至凌晨的餐馆也准备打烊了。后厨清扫的阿姨收拾了用了一天的抹布,泡进水里,一边心疼一边往水里添洗洁精,“洗洁精贵的呀。”
企台分了小费,王潜龙又碰到了一个抠门的食客,甩着手里的单子对我埋怨,“这个社会,就他妈是笑贫不笑娼。”
月亮升起,就又算是过了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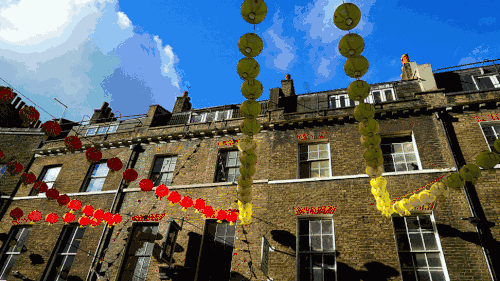
福州的佛教文化很浓,据载,有个地方官先后舍钱90万贯修建寺庙,算上周围的县区,有着大大小小700多座。福州“城里三山千簇寺,夜间七塔万枝灯”,是为一景。庙内供神,香火不旺。塔也成为了只在夜里闪亮的地标建筑。
福州人没有将佛教带到美国,但是他们却好像被某些从中国来的东西绑在了中国城这条街道上。
曹阿婆七十一岁,在唐人街街角开了一家精品店,这条路,她呆了几十年了,“中国城除了房价翻了几倍,没有什么变化。”每天看店的时候,阿婆都放着《情深深雨蒙蒙》打发时间。十八岁的阿强,二十五岁的李哥,三十岁的乔哥,都和张申凡一样过着“上班炉头,下班枕头”的生活。
凭借一代又一代人的韧性,来自中国的偷渡客终于在美国建造了一个他们熟悉的,一应俱全的社会。除了钱,和面子,美国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也从不试图探寻更多,守着这条街和自己熟稔的价值认定,十年二十年就如此度过了。
大概美国天空悬着的,还从前生活的那个太阳,太阳底下无新事。
我从福州坐车,辗转去了张申凡的老家,贵安村里福州市30公里,依山傍水,被建设成了一个温泉度假的圣地。我找了家曾经被报道过的当地幼儿园,五年前的新闻说这里就读的孩子一大半都是美国国籍。周二,学校孩子已经放学了,门口的保安是洛阳人,跟我说,“贵安现在是淘宝村呀,县城里多的是跑来做电商的,开农家乐的外地人。你说的移民已经移干净了。”
我在幼儿园的斜对角找了家30来平的小餐馆,店主是一对70来岁的老夫妻,都是贵安人。爷爷普通话不好,但是热情,我去时不在饭点儿,他一边摘着小葱一边跟我开玩笑,“你们小孩子读书多,但是不知道有时候书里也会骗人的。美国其实有52个州,50个州加上温州和福州。他们温州人买房子,我们福州人开餐馆的呀。”
店里收银台的边角儿贴了张周岁小孩的照片,爷爷的大孙子周岁的时候在洛杉矶唐人街拍的,他又笑着说,“我是美国人的爷爷。”
阿婆从洗好的小葱里抽了两根儿,切得细碎。沸水里烫熟一漏勺线面,小白瓷碗装上各类的油盐酱醋,混着葱末拌好了给我,收了我4块钱。福州这种没有卤的面,对于一个北方人来说,真是过于清淡了。
食,是福州人在美国赖以生存的方式。随着时间的积累,青春换成了钱,味蕾里小葱清油拌出的一碗家乡味,被中餐馆里重油重盐的川味取代了。“家”模糊成了一个概念,从离开的那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福州人,也必然不会成为梦想中的美国人。
本文收录在NEBULAR第二期杂志
点击下方图片获取更多杂志详情


作者:权子
采编:王静远 权子
美编:阮佳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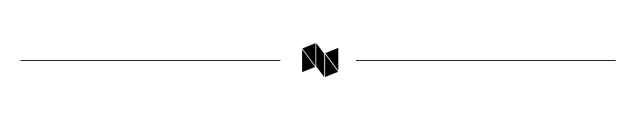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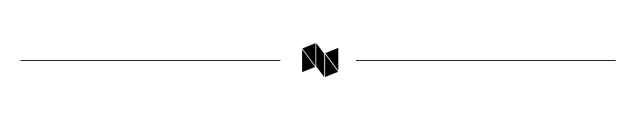
人|故事|經歷|青年態度
北美新媒体平台
N E B U L A R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