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民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 学术剧8.8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作者:段德敏(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
1定义“民主”的尴尬
什么是民主?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唯一能确定给出的答案似乎是: 我们没有确定的答案。在当代,这一问题之所以令人着迷,主要是因为它和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即“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对大多数人而言,“民主”不是人类社会多种可以选择的政体中的一种,而是“那种”政体或政治生活形式,它承载着人类社会应该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由于这种政体之“是”和美好生活之“应是”之间的结合,给“民主”下一个恰当的定义自然就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美好的价值目标实在太多,有时候互相之间还有冲突,实在不好做一个万全其美的概括。

事实上,无论怎样定义,都会有人不满意:民主要有公开的选举?有时候有选举也不一定有民主,很多独裁者都是被选上去的;民主要有不同政治力量(如政党)之间的公开竞争?有时这种竞争会导致社会内部的撕裂和冲突;民主要有法治?法律始终有“良法”和“恶法”之间的区别,况且“法治”的定义本身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东西,借用法治来定义民主几近于套套逻辑。这种定义和反定义之间的较量可以无限进行下去。丘吉尔对民主有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说法:“民主是人们试过的所有政府形式中最不坏的”(完整原文“No one pretends that democracy is perfect or all-wise. Indeed, it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ose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看似解决了上面的问题,但其实并没有,因为“最不坏”其实就是人目前能够做到的“最好”,但具体“最好”在哪里?丘吉尔没有说,估计也说不清楚,所以巧妙地用“最不坏”这样的修辞来给出一个答案,我们听了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

丘吉尔
以上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需要如此这般地定义民主,事实有些定义——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著名的《论民主》(On Democracy)中给出的定义——确实能为我们认识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不错的帮助。但世间之事大多经不起“认真”二字,如果我们细究,特别是在无限多样的历史事实和未来可能性的帮助下细究,任何定义都免不了“不够完美”的尴尬,糟糕的时候还可能会自相矛盾。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另一种思路来看待“民主”,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或许民主还有另一种打开方式。
2民主的“阴暗面”?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大部头著作《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就是打开民主之“另类”方式的一种。为什么说它是“另类”?从其标题就能看出大概:民主具有“阴暗面”,它还跟种族清洗有关。乍一看这似乎是批评民主政治的书,但稍微翻阅其内容就知道并不是这样。因此有的评论最后会抱怨曼这样说民主不公平,他所说的种族清洗其实怪不到民主头上,所有实行过种族清洗的政权或国家其实都是不民主的,或是起码不够民主的。这实际上是上述民主定义情结的延续:民主一定是和某种规范性的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和“阴暗面”挨不上。如果我们把这一逻辑再往前推,可以说“民主的阴暗面”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oxymoron),就像“黑色的白玉”、“长方形的圆球”这类说法一样不具有任何实在的意义。然而,这显然不是曼的意思,他在书中这样明确地表达他的主要观点:“谋杀性的种族清洗是现代的,因为它是民主的阴暗面。”在另一处,他说:“种族清洗是伴随着世界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而大规模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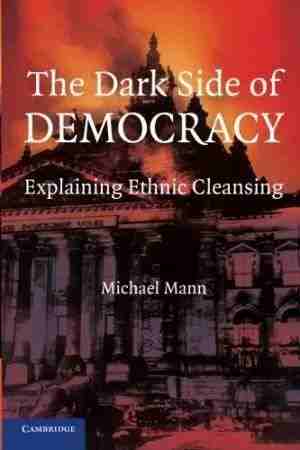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
这里的关键词是“现代”或“现代化”。事实上,与上述曼的主要论点相互包含的另一个重要论点是,种族清洗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象,它与现代性有关。那么古代社会是否就没有种族清洗?这听上去好像有点问题,因为古代大规模的屠杀并不罕见,往往比现代社会的杀戮残酷得多,有些好像也是针对某个族群的,比如我们可以就近举清军入关屠城的例子,较远的如古罗马攻占迦太基后的报复性屠杀,等等。但曼认为这些都构不成种族清洗,原因主要在于古代社会中的上层社会(或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别极大,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本身几乎就已构成两个不同的族群。种族清洗一般是指一个民族针对另一个民族采用屠杀、放逐等方式清洗,古代社会既然内部阶层区别巨大,其本身构不成一个民族,因而也就谈不上针对另一个民族的清洗。古代上层精英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土地和臣民,后者是他们争取的对象,而不是消灭的对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有效的征服,他们有时需要杀掉很多人,但其目的是为了取得稳固的统治,而不是将某些人看作“污点”从社会内部清除掉。清军入关屠城就是如此,它是满人上层为了取得对大片土地的统治权而采取的行动,而满人精英自己却很快就主动地吸收了汉人上层的儒家文化,在之后的几百年中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汉化。反观现代社会的种族清洗,发动清洗的一方几乎都会认为被清洗一方的文化或信仰是低级的,他们绝不可能主动地向对方学习。因此,曼引用罗杰•史密斯(Roger W.Smith)的话说:“古代的战争中人们一般都是因为他们‘在哪儿’而被杀,不是因为他们‘是谁’而被杀。”

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发生了三次战争。
曼对现代社会的种族清洗有大量的记录和分析,但它们的发生大体都有一个历史前提,即社会的大规模平等化,或人与人之间身份的拉近。较遗憾的是,曼在这本书中对这一点没有明确而又详细的论述,但我们从字里行间仍然能看出来。曼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中,最接近种族清洗的历史事件几乎都与某种救赎宗教(salvation religion)有关,因为这种宗教有一种“民主化”的效果,它通常会将所有人——无论其身份、阶层、地位——都纳入同一个精神共同体中。一神教在这方面走得更极端一些,而更为强调灵与肉之区分的基督教尤甚。在基督教那里,尽管在尘世中人们分成不同等级,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他们在将来也会受到平等的审判,这种超越阶层的普遍信仰让他们在中世纪时期就结成某种类似现代“民族”的群体,从而也使得他们也对不同信仰的人群更不宽容。曼说:“(在历史上)基督教成了所有救赎宗教中最不宽容的一个,它催生了很多宗教清洗,杀人不是因为对方‘在哪儿’而杀,而是因为他们‘是谁’而杀。”(引自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反观古代的伊斯兰教,恰恰是因为其“民主化”程度不那么高,历史上的穆斯林帝国对其他宗教反而相对较宽容。奥斯曼帝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其统治的鼎盛时期,基督徒和犹太人虽然地位不高,但都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帝国的统治阶层有用。只有到了近代民主化之后,在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之时,“土耳其人”作为一个民族才开始大规模的排外,其顶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境内亚美尼亚人的屠杀。

穆罕默德二世及其军队进入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由救赎宗教带来的民主化仅止是“灵魂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the soul),现实中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仍然有着巨大的鸿沟,而这一鸿沟的逐渐消退的过程也是现代化的开始。社会阶层之间距离的拉近使人们越来越将自己想象为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近代以来技术的进步、文化的传播、交通的便利、经济水平的提高等等都对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直到1870年代,法国大多数农村居民(巴黎周围地区除外)都不把自己看作“法兰西民族”的成员。(曼引自Eugene Weber, Peasants intoFrenchmen)现代化的一个巨大效应就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建立起一个个同质化的“民族”,这些人称自己为“人民”,并要求政治权力做出巨大改变以适应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要求。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既是民主革命的高潮,也是法兰西民族主义正式出炉的标志。从欧洲扩张到全世界的民主革命的最大后果之一是建立起了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几乎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国家(state)被理解为“人民/民族”利益的代理人。但问题在于不可能所有国家都与某个单一民族对应,当一个国家(country)内部出现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时,“人民主权”很可能会转变成“多数民族主权”。这便是现代社会种族清洗的历史前提,也是“民主的阴暗面”的由来。
正如曼所说,“人民”(thepeople)在词源上既可以指向古希腊语中的“平民”(demos),也可以指向“民族”(ethnos)一词。近代欧洲的民主化过程中也极具多样性,西欧和北欧的国家大都以制度化的方式保留了人民内部的多样性,因而更少种族清洗。但东部和中部欧洲就没那么幸运,在那里“人民”最后经常就变得与某一个民族或种族重合,因而种族清洗也更为频繁。然而,前者所建立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海外殖民统治时却又充分暴露了现代民主国家的种族清洗潜力,典型的如美国国家权力对印第安人的驱逐和屠杀。无论其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如何有效,他们在面对野蛮落后的“土著”时,清洗很多时候就成为一个方便的选择。
3托克维尔的“民主”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民主的阴暗面》一书标题中的“民主”大概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它们能把该“民主”和一般意义上的、作为某种价值目标的“民主”区分开来:第一,同种族清洗是现代现象一样,民主实际上也是一个现代现象;第二,在任何所谓现代民主国家中,“人民”(demos)和“民族”(ethnos)之间的界线并不那么清晰,从“自由民主”向“种族主义民主”或其他形式的压迫的转化比我们想象得要容易得多。实际上曼不是第一个这样使用“民主”一词,的,早在19世纪早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就以类似的方式构建其关于现代社会与政治的理论,只不过他对“民主”本身的思考要系统、完整得多。

托克维尔
很多人将托克维尔看作近代西方“最重要的”——如果不是“之一”的话——“民主支持者”,相应地,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也经常被看作讨论美国民主制度的书。这是巨大的误解,托克维尔并没有支持“民主”或为其辩护,他甚至对“民主”抱有极强的敌意,《论美国的民主》也不是讨论美国的民主制度如何的书。这里的关键在于“民主”(democracy)一词在他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论民主》(On Democracy)中给“民主”下了相对清晰简便的定义,它包括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成年人的公民资格等等。我们今天对作为一种制度形式的民主的理解虽然可能与此不完全一样,但大体差不太多。但这与托克维尔对“民主”一词的使用相差甚远。从达尔式的民主概念出发,我们大概可以说“民主的反面是专制(despotism)”。但我们只要稍微仔细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就会知道,他几乎从未从“专制Vs.民主”这一角度来使用“民主”一词。在他那里,与“民主”相对的是“贵族”或“贵族制”(aristocracy)。当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绪论中说“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时,他也并不是在预言达尔所描述那种“民主制度”是不可抗拒的。他是在说一种新的、他称之为“民主”的“社会情况”(socialconditions)不可避免。那么这个“社会情况”是什么?托克维尔称之为“身份的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即人们在身份上不再存在“贵族与平民”这样的等级区分、人与人之间普遍平等的状况。这里的“平等”并不是指人们在其所拥有的财富、权力或受尊重程度上的平等,这些方面的不平等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恐怕永远也不会消失。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是这样一种社会事实,即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相似,古代社会中将人与人区分开来的阶层之间的巨大鸿沟——贵族与平民之别——逐渐消失,任何人都可以和有机会成为富人、有文化的人或有权力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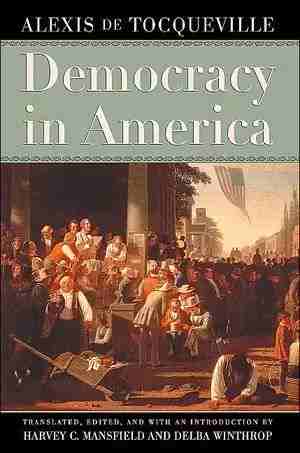
《论美国的民主》
在“古代与现代”、“贵族社会与现代社会”区分的基础之上,托克维尔展开了极具洞察力的分析,其洞察力在很大程度上又跟他对这一转变的观感和态度相关。出生在法国大革命后的托克维尔得以目睹以革命为名的种种暴力、灾难和混乱,他个人出身贵族世家,其家族许多成员都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革命党人处死,其父母幸免于难,仅因为其临刑前恰逢罗伯斯庇尔倒台。他对“民主”的基本态度是:一方面他接受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变,认为它“有如神意”,不可抗拒;但另一方面他对新社会的到来并没有什么多少正面的期待。他说“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主要是因为他看到,如果任由民主社会按其本性发展,人类社会可能会走向一个极为阴暗的方向。现代社会的身份平等把个人从传统的社会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表面上看这给了人们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但这个过程同时也取消了将人与人之间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纽带,将个人直接暴露在了国家权力之下。事实上,个人越“解放”,他/她作为孤立的个体也越软弱,国家权力也就越可能走向绝对化。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平等化和王权的绝对化是互相支持、相辅相承的关系,大革命本身非但没有改变这一点,反而将“绝对国家权力”在新的形式下推向更高的层次。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平等与自由之间的矛盾”。
托克维尔曾用“民主时代的专制主义”(democratic despotism)一词来概括对民主社会所可能导致的压迫,并称这种专制与“至今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均不相同”,而且“当代人在他们的记忆中也没有这种压迫的印象,我曾试图用一个词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压迫所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而未成功。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词汇,都不适用。”那么这种压迫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摘取其中一段加以说明: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本)
可以说,这是托克维尔版本的“民主的阴暗面”。想象一下,如果他活到20世纪并看到以德国纳粹为代表的现代灾难,相信他会对“民主时代的专制主义”有更新的理解和更升级版的描述。不过好在受他影响很深的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后来继续了这一工作,她对 以德国纳粹统治为代表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尤其是纳粹政权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做了极为深刻细致的分析。同样,阿伦特也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

汉娜·阿伦特
4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
很多对民主的定义和关于民主的讨论都喜欢把民主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包括罗伯特•达尔,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毕竟一些制度形式——如公民集会、选举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些讨论中也有不少花了一些功夫去辨别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区别,如享有公民资格的人的范围、制度发达程度等方面的不一样。但这些讨论大多忽视了二者之间更为本质性的区别。在古希腊,所谓“民主”只是多种可能的政体中的一个,而且它远远不是最好的那一个。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很好的记载和论述,城邦的统治形式有更高的标准,民主或平民统治——其最大特点是依(公民)“数量”统治——显然不是最好的统治,君主制、贵族制完全有可能更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曾说过“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在他以及当时人们的眼中,这是一种“自然”。换句话而言,奴隶如果凌驾于主人之上或跟主人平起平坐,这才是“不自然”的。同样,对城邦的统治而言,也存在一个更高的“自然”,作为政体形式可能性之一的“民主”与此“自然”之间有着极大的距离。在欧洲中世纪时期,世俗统治之上同样存在一个更高的“自然”或标准,此即“上帝”。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一定要将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相比较的话,古希腊的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与中世纪时期的神权政治更为接近。

现代民主的前提是身份的平等,在这一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人民”自己统治自己的要求几乎已成为唯一的可能性,即便是所谓“专制”政府也需要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之上,告诉人民自己只不过是作为“人民的代表”进行统治。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同理,现代社会“专制”的根源通常也并不在于或不仅仅在于专制者本身的邪恶,它还跟“人民”内部的构成和机理有关,正如曼所展示的demos和ethnos之间的区别及其各自可能导致的后果那样。体认这一古今之别对理解现代民主至关重要。当代很多关于民主的研究都建立在前文所述的单一的、带有强烈规范性的民主定义基础上,它们通常不能成功地解释概念和社会存在之间的巨大差别,任何这类对“民主”的定义——无论它如何复杂周到——都很容易遭到自己所列举的事实的反驳。(作者:段德敏;编辑:胡子华;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段德敏,男,1982年生,江苏溧阳人,博士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系伦理、社会与政治哲学中心,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比利时鲁汶大学政治哲学研究中心(RIPPLE)研究员、欧洲大学中心(EUC) co-director,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民主理论等,已出版英文专著一本,在国外、中国大陆和香港多家知名期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并曾受邀在国内外多家大学和研究机构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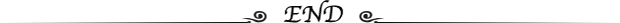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