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为什么会签定“不平等条约”?丨检书166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条约制度改变了传统的中外关系,它既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害,蒙受着不平等的耻辱,又随之带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和部分体现平等原则的内容。这是一段艰难曲折、充满屈辱的历程,对清政府而言,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既要承受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的特权制度,又要舍弃对他人不对等的天朝体制,在阵痛中剥离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接受近代国际关系模式。
从鸦片战争开始,毫无近代条约知识的清政府,对这一新的关系处于朦胧的状态,缺乏必要的认识。它所面对的已不是传统的周边“夷狄”,而是有着更高文明的海外征服者。长期封闭的清朝大吏们颟顸无知,对国家主权、国际法,以及近代国家交往的原则和方式等一无知晓,他们仍然用封建时代的帝国观念和手段认识和处理对外关系。对于条约的谈判和签订,清政府采取了漫不经心的态度。伊里布向黄恩彤传授经验说:“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英国人利洛(Granville G.
Loch)在《缔约日记》中对这些谈判大吏做了这样的描述:“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的字句与语法。中国代表们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因此等他承认条约以后,就要求大臣将运河中的船只转移到江中。”清朝君臣不知道和约与商约的区别,将结束鸦片战争订立的条约视为一揽子解决争端、一成不变的万年和约。道光帝说,“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从此通商,永相和好”。耆英也认为,“惟一切善后事宜,尚须明晰妥议,立定章程,尽一办理,方可期一劳永逸,永杜兵端”。中英战争结束不久,美国便要求订约,而仅将条约视为解决两国争端和约的清政府,根本没有建立条约关系的打算,也没有这一观念。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对美也要求订约很不理解,答复说:“英咭利与中国构兵连年,始议和好,彼此未免猜疑,故立条约以坚其信。若贵国自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商人之来粤省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本属和好,何待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
清朝官吏们也不懂得,条约是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在他们看来,与外国订约就是给予对方权益,是单方面的让予,如果再行修约,意味着还得继续给予对方以新的权益。清政府将已订条约视为一成不变,担心失去更多的权益,其基本原因便在于此。美国全权公使顾盛在《望厦条约》中塞进了12年后修约的条款,从条约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任何条约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清朝大吏们只希望维持现状,谈不上通过这一条款提出自己的条约要求。当列强提出修约时,清朝君臣无不以“万年和约”为辞,极力反对,谓:“前立和约,既称万年,何得妄议更张”;“既系万年和约,似不应另有异议”;“均应遵照旧约,断难随意更改”。咸丰旨称:“既称万年和约,便当永远信守。”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如果彼坚执12年修约,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后来薛焕更明确地说:“臣思外国条约,经一次更改,即多一次要求,议令立约后永远遵守,暗中消去十二年为度一层。”
在被迫接受条约之后,清政府采取了信守条约的方针。这一方针包括自己守约和要求对方守约,如耆英所言,“如约者即为应允”,“违约者概行驳斥”。从总的趋向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守约方针,主要是针对对方的,而且还有着暗地摆脱条约约束的明显意图。清帝国的君臣将接受条约视为羁縻外夷的权宜之计。开始,它也是施以兵威,待征剿受挫,道光只得“聊为羁糜外夷之术”。订约中它给予列强的某些条约权利,包括一些重要特权,与传统的羁縻之道相吻合。例如,开放五口,以及给予其他相关的通商权利,便符合施之以恩惠的羁縻之道。“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而帖服。”他们担心列强纠缠不休,认为,“所赖通商为该夷养命之源,税例之增减多寡,即关夷情之向肯从违,若过为搜剔,则恐致反复”。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这两项重要的条约特权,也与羁縻之道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清政府开始主动要求修约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官吏们开始有所醒悟,对新的条约关系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作了某些调适。
由于列强各国更加苛刻地要求清政府严格履行条约,锱铢必较,清政府的守约方针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列强各国对各省官员忽视条约极为不满,1862年1月,英国公使卜鲁斯(F. W. A. Bruce)即向奕呈递数千言的照会,谓:“两国始终不和之缘,总由各省督抚于外国交涉事件,并无尽心守约之理”。“各大吏向不存秉公尽约之意,转以条约准行之处,多方推卸,设法阻挠。”“外省大吏任便自行,或不谨守约条,或敢私为改易,殊非内外友谊之道,实易开嫌隙之源。”照会列举了地方官不遵条约的种种事例,要求“大皇帝明降谕旨,示以各国条约,原为慎重之文”。“外官只须尽约照办,锱铢勿许增减”,“敢有相违者,立予重处”。在指责清政府未能守约的同时,列强又施以威胁手段。在照会中,卜鲁斯声称,“此种背约阻滞,无非致令贵国临险之虞……
毕至酿成称戈之祸”。各国“总以将来中国不能守信为虑”,其后又屡屡指斥清政府,处心积虑“欲使中国家喻户晓”。如1863年,英、美、俄等国在法国的支持下,分头向奕递交一项声明,对各省执行条约的状况表示不满,并向清政府提出警告。

第10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1841-1845),任职期间,同中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美国通过这一条约获得了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同治初年,由于潮州进城和田兴恕两案,列强各国怀疑中国不肯按约办理。加上此时发生追偿欠款案,英国更以此“为发端辩难之据”,态度极为强硬。照会谓:“深虑终使外国忍耐不堪,徒向地方官屡屡照会,置若罔闻,必致自出妥速之法”。照会以“自出妥速之法”相威胁,表明英国是势在必得,甚至不惜用暴力手段来强迫清政府恪守条约。奕等甚感问题严重,主张迅速解决。根据奕的意见,朝廷即刻谕令两广总督瑞麟亲自办理此事,同时又颁发一道严厉的谕旨,斥责该省督抚不按条约办事,强调遵守条约的重要性,指出:不遵守条约“致口实愈多”,不能“使人心服”,后果严重,“设令肇衅,则广州之前鉴不远”;“万一该国不能忍耐,恃强入城,与国体更有关系”。只有按约办理,“俾该领事得以按约进城,用符定约,方可以示诚信”。鉴于事情的严重性和急迫性,上谕口气极为强硬,不容商量,谓此事“势在必行,如或延阁,惟瑞麟是问”。经此事件,清政府遵守条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朝廷的态度明确起来,而且一些地位显要的地方督抚也都强调取信于洋人,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重视履行条约义务的主体意识。
与此同时,随着中外交往的建立和扩大,西方的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准则等从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清朝大吏们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1864年,清政府刊印了丁韪良(W. A. P. Martin)翻译的《万国公法》,奕上奏说,“该外国律例一书,衡以中国制度,原不尽合,但其中亦间有可采之处。” 一方面,他们对条约制度及其性质的理解,具有了一定的国际法意识。奕谓“昔日允之为条约,今日行之为章程”。署湖广总督、江苏巡抚李瀚章更确切地说:“今日之约章,即异日之法守。”
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李鸿章指出,此“系条约而非议和”。修约是双方的权利,“有一勉强,即难更改”。“其有互相争较,不能允从之处,尽可从容辩论,逐细商酌,不能以一言不合,而遽责其违约。”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对其“上侵国家利权,下夺商民生计”的种种非分要求,“皆可引万国公法直言斥之”。另一方面,他们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到现存的条约制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清政府明确表示:“查中外时势,有难有易,且亦各有国体及自主之权。如时势可行,及无碍国体政权者,中国原有自主变通之法。其窒碍难行者,无论不能勉强,就令勉强试办,终必无成。”也就是说,如无碍国家主权,可以变通,相反,即使勉强试办,也终必无成。其后到光绪年间,他们更明确从国际法的角度,来检索此前所订条约的失误。如李鸿章奏言:“从前中国与各国立约,多仓猝定义,又未谙西洋通例,受损颇多”。
对条约本身的认识以及对西方列强“修约”要求的应对,又进一步发展为主动修约的思想主张。例如,曾纪泽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认为,通过不断改订不平等条约,就可以使中国收回权利。他看到,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长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前者是指“分界”条约,后者是指“通商”条约。中国也要利用通商条约的这种性质,不能独为对方所用。“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深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不善,正赖此修约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曾纪泽认为,改约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至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这样中国可以不着痕迹地收复权利。按照西洋通例,“虽蕞尔小邦欲向大国改约,大国均须依从,断无恃强要挟久占便利之理”。1881年,曾纪泽曾赴英外交部,“谈商改条约之事”,“争辨良久”。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官员亦有类似的认识。1884年,总理衙门还向各国明确表达了修约的期望,表示:“惟我中国办事,均系十分遵约,一本万国公法而行。即如前与各西国所立各约,其中原有中国未尽出于情愿,勉为允许者,谅各国大臣亦所素悉。中国则于明知各约内之有损于国,无益于民者,初未尝或有不行照办,不过期望各西国渐渐可以改为和平。”其后,清政府虽未明确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但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的权益,并有意识地在新订条约中消削或限制此前已被列强所攫取的特权。
三、甲午战争后,讲求外交之道渐成风气
经过甲午战争,伴随着中国藩属体系的崩溃,清政府摒弃了宗藩观念,并更注重守约,进一步加强防范,以“见信于洋人”。另一方面,列强侵略的加深,又使得清政府更为愤恨。他们感到,“事事退让之路已经走得太远了,从今往后,抵拒外国的侵扰应该成为它的政策的主旨”。清政府尤其是其内部的顽固势力,长期以来试图“驱逐洋人”,摧毁条约关系,但对外战争的屡屡失败,不得不“暂事羁縻”。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声势浩大,又有种种“神术”的义和团的兴起,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认为这是上天赐予的千载良机。载勋等谓:“我看他们正是上天打发下来灭洋者,缘庚子至庚子,渠等在中国搅扰已一甲子,此时正天收时也。”这种“天之所使,以助吾华”的论调,附和者又“神奇其说”,造成了清廷的主导倾向,“盈庭聚论,众口一词”。“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词”。于是,清政府利用义和团实施了前所未有的排外,显示了不愿接受现存条约关系的倾向。

《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降服图》
然而,列强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将“惩前”与“毖后”相结合,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思想等方面,全方位地巩固和强化了中外不平等的条约制度。经此创巨痛深,清政府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击,对条约关系的认识更推进了一步,并作了更大力度的调适,更为全面地接受了这一新的关系。除了强化守约意识之外,清政府的对外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更为主动地“以夷变夏”,传统的羁縻之道转向近代性质的条约外交。1901年1月,光绪和西太后还在西安,便下诏维新,要学“西学之本源”,“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还要“浑融中外之迹”,举凡“朝章国政”等等,进行全面改革。清政府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以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自行“以夷变夏”。
各级官吏研习国际法和条约,讲求外交之道,亦渐成风气。如1902年,直隶州知州曹廷杰将《万国公法》“逐条注释”,名为《万国公法释义》,请吉林将军长顺“咨呈外务部核阅”,并“请旨饬部删定”,“颁发学堂”,“为诸生肆习公法触类引伸之助”。驻意公使钱恂提出仿各国通例,“组成一研究会”,研究海牙公约;又主张将条约之译文,国家之成见,编订成书,颁行国内,作军事学校的教科书。其他官员提出了类似的建议,或主张将各国律例条约“详加编译,分类成书”,“以备研究”,或主张汇刻中西成案,“发给内外各衙门办事人员,悉心研讨”。张荫棠奏称,对外之方,“其要在于毋忽略国际公法”。还有的提出“设外交学”和“专门外交学堂”,等等。外交、公法等还被纳入科举考试范围。严修提出改革科举,设经济特科,“约以六事”,其二为外交,“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者”,获得允准。1903年殿试,清廷将外交、公法等作为策试内容。
不少大吏更进而从国际公法的角度反省传统的对外观念,认真探究条约关系,各省愈益重视条约的编纂刊印。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其所组织编辑的《约章成案汇览》序中说:“凡一国之法律,必有立法者以裁制之,惟国与国交际之法律,则无人能擅立法之权,故居今日国际法之主位者,莫如条约。” 方今环球大通,世变日亟,“前车已逝,来轸方遒,杜渐防微,阳开阴阖,讵复有常辙之可循。”山东巡抚杨士骧认为传统的对外之道是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主张正确认识和对待条约关系,谓:“古今天下之趋势何归乎?一归于法治而已矣。”“吾国开关之始,士大夫狃于闻见,其视梯航而至者,莫非纳款贡献之列,交接之仪辄不屑以平等相待。外人以公法为辞,谢不肯应,其后屡经惩艾,不得已曲徇其请,割弃利益,欲返求公法以自全而已,无及矣。故国际共享之利,我独不得与,而中外交涉之历史,大抵失败之迹焉。”他提出,要如日本一样“壹意维新”,“修政经武”,对条约须“谨而持之,以谋其便,化而裁之,以会其通,异日国运之振兴,必有赖于是者”。驻美公使张荫棠批评传统的驭夷之道,谓:“窃维吾国向来一统自治,闭关日久,士大夫多昧于五洲大势,遇事习为虚骄”。他认为,清政府外交失败,列强之“威胁强逼,智算术取者半”,当局“不解国际法律自误者亦半”;提出对外之方,“其要在于勿忽视国际公法,勿放失土地主权,勿懵昧于列国情势而已”。并指出,外交条约,“外以持国际之平衡,内以保国民之权利,正宜得多数才智,各竭其心思之所长,经历之所得,以资裨补”。他进而提出,“宜先准资政院议员行协赞结约之权,又于院中设专科委员会,予以审量外交事务之权,引起国民关心大局,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外交之后盾”。这些说明,清朝大吏们对条约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修约要求更明确提了出来。驻俄公使杨儒提出效法日本,改革内政,以修改约章,“保权域中”。安徽巡抚王之春主张“将考究条约一事,列为司员考成,及内外情形了然于中,得以预筹修约”。端方以“西人商改条约,向以十年届满之日为紧要关键”为由,提出修改《辛丑条约》有关驻兵和禁止华兵在天津二十华里屯扎的条款。在修订商约交涉中,中方代表突破《辛丑条约》仅规定对方有权提出修约的限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谓:“既有商议二字,便是彼此可以商改。”他们在诸多方面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尤其是促使英国等允诺在条件成熟时放弃领事裁判权。
传统的驭夷之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走向了“以夷变夏”,羁縻越来越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用词。在道光、咸丰、同治三朝,这个词可说是俯拾皆是,充斥于君臣的上谕和奏折中;而在光绪朝以后,这个词便不多见了,尤其是庚子之后更为罕闻。“不屑与交涉”“不屑与交际”的旧习逐渐消退,朝野“竞起而讲交际之道”,甚至“上自宫廷,下至地方官吏,其所以与外人交际者,宴会馈遗,无不竭力奉迎,以求得其欢心”。中国外交正在发生着根本的转折,传统的观念和制度,逐渐被以条约为内核的近代外交所取代。不过,清末的变化仅仅是这一全面变革的开端,羁縻意识仍然并未彻底抛弃。“今以中国现象言之,国际观念最为幼稚,较其程度,尚在排斥主义之终期,与相互主义之初期”,拒外、畏外和媚外心理并存。大多数人对条约公法和国家主权的认识,仍然是一知半解,“此皆平等观念尚未萌芽之故也”。尽管如此,中国外交已出现了新的趋向,传统的驭夷走向了近代的外交。
(本文系《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6年9月出版 第四章“条约制度的建立及其影响”第三节内容,已经出版社授权。编辑:李大白 陈菲。文章标题和文内小标题、图片均为编者所加。)
图书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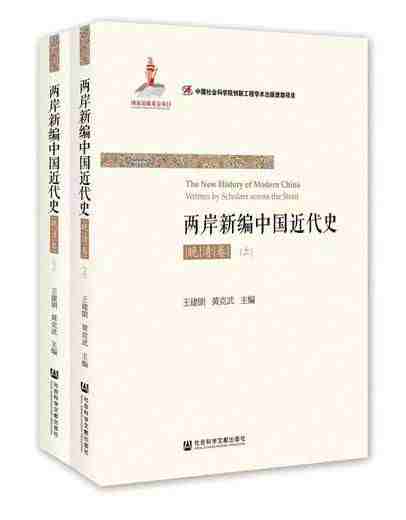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册书是由两岸近代史学界合作撰写的中国近代史(1840-1949),参与者共57人。全书分晚清卷和民国卷,各卷又分别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通史,下册为专题史。本书论述了近代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展示了自1980年以来近代史方面的新研究成果。本次推出的是晚清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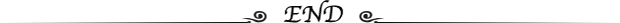
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授权,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欢迎朋友们转发至个人朋友圈,分享思想之美!
关注我们,可在微信里搜索ThinkerBig添加公众号,或长按下方二维码识别添加订阅。
微信公众号已开放置顶功能,欢迎您在本号设置页面里打开置顶开关。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