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尔盖斯 | 伊斯兰国的崛起——以及怎样打败它

王立秋 /译
要理解伊斯兰国(IS)的突然崛起和它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的领土扩张,把这个组织放到更广泛的,全球吉哈德运动的语境中去看,是很重要的。
特别地,我们必须考察它所由来的那个组织——美索不达米亚的基地组织,即一般所谓的伊拉克基地组织(AQI),伊斯兰国就是从这个组织生长出来的。
在2003年和2010年间,为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所触发的权力真空和武装抵抗,以及萨达姆·侯赛因的之前占统治地位的复兴党及伊拉克军队的解散,给AQI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给了它渗透当地越来越脆弱的政治体的机遇。
然而,AQI的迅速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特别地,有两个事件威胁到了它的扩张。
2006年,塞莱菲-吉哈德团体与逊尼派阿拉伯部落领袖——后者为前者在其统治区域强加的恐怖与极端统治所激怒——的冲突,触发了一场内部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导致当地部落与美国的合作正式化。
同年,AQI的创建者和头目艾布·穆萨布·扎卡维被美军击毙,对这个好战的激进组织来说,这标志一个收缩和衰落的转折点。
在一个过渡时期后,2010年,艾布·巴克尔·巴格达迪被任命为AQI的领袖。
军事经验
巴格达迪的上台,与伊拉克高度极化的政治形势分不开:中央政府在政策上边缘化、贬损逊尼派穆斯林社群。
当时,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基于教派的政策也被视为是受伊朗影响的结果,这就使巴格达迪得以占据这样的立场,去把AQI重新组织为逊尼派反对巴格达的什叶派政权的先锋组织。
巴格达迪的指挥,在多层面上改变了这个组织的做派。

他通过招募来自前萨达姆军队(特别是共和国卫队)的有经验、有技巧的军官,来完成军事架构的重组,这些军官把伊斯兰国变成了一支职业武装力量、和一架潜在的杀戮机器。
根据伊拉克方面已知的消息,巴格达迪所仰赖的军事委员会,就包含八到十三名前军队官员。
他也是少数很早就认识到叙利亚危机的重要性,及其可能从那里的政治混乱中获得的好处的高层吉哈德主义者之一。事实上,也正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冲突,使巴格达迪得以把AQI重建为一个强大的集团。
艾布·巴克尔·巴格达迪:一个神秘的领袖:
关于伊斯兰国的领袖艾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我们所知甚少,而且我们也很难把关于他的神话和现实分开。
伊拉克的追随者们宣称,巴格达迪是巴格达伊斯兰大学的博士,他的研究领域是伊斯兰文化、历史、沙里亚和教法学。
他们据此而把巴格达迪描绘为一个文人,在宗教上学识渊博,有资格担任全球穆斯林共同体或者说乌玛的哈里发或领袖。
然而,认识巴格达迪的人的说法则不同,根据这些人的描述,巴格达迪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出生于巴格达北部著名的“逊尼派三角”的萨马拉城,他脾气暴躁而喜好冲突,经常从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
不管巴格达迪个人的故事如何,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他自我激进化、向好战分子转变的过程,发生在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在那个时候,他被关进了美国的军事监狱。
他在2004年到2005年间,在伊拉克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乌木卡萨尔附近的布卡营被美军逮捕收监,罪名是,他是逊尼派“步兵”。
也就是在这里,他得以见到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吉哈德好战分子,并与志同道合的宗教极端分子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网络。
在布卡营,巴格达迪也遇到了以前萨达姆·侯赛因军队的军官,这就给吉哈德分子和前复兴党成员之间的不神圣的联合做好了准备。
当2011年美国撤出伊拉克的时候,AQI最多只有几百个追随者——而现在,伊斯兰国最小支系的军队的士兵数目也在一万七千人和三万两千人之间。
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在基地组织如日中天的时候,基地组织中央所能召集的士兵人数,也不过一千到三千人,这个事实表明,(基地组织的)跨国吉哈德主义与其伊斯兰国变种的“近敌(near enemy,相对于美国这样的远敌)式的”、或者说地方吉哈德主义相比是多么地有限和弱小。
吉哈德分子之间的战争
2011年,巴格达迪派遣他的手下艾布·穆罕默德·约拉尼到叙利亚,在这个被战争蹂躏的国家组织一个吉哈德分支组织,这最终导致了努斯拉阵线的建立——即,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
叙利亚不仅为巴格达迪的组织提供了一片补充武器、人力、资源的沃土,该国社会结构和政治系统的解体,也为伊斯兰国的吉哈德分子提供了动机和灵感。
该组织领导层的分裂于2013年显露。
巴格达迪号召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建立一个伊斯兰国(ISIS或ISIL),这就意味着,AQI和努斯拉阵线将合并。
约拉尼拒绝合并,这一举动得到了他所效忠的,基地组织的大头目,艾曼·扎瓦西里的支持。
于是在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之间爆发了一场吉哈德分子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杀死了成千上万名战士,并暴露了巴格达迪及其先前的导师扎瓦西里之间的激烈的权力斗争。
如今,伊斯兰国已经接过了全球吉哈德运动的领导权,使它出身的那个组织变得黯然失色。
其残忍和恐怖——这归根到底出自于伊拉克沾满鲜血的现代史——远远超越了最近几十年来的前两次吉哈德浪潮中的任何一次。
伊斯兰国的邪恶反映了真主党数十年统治留下的苦涩遗产:它撕裂了伊拉克的社会组织,给这一地区留下了还在恶化的深刻伤口,并使吉哈德的第三次浪潮农村化了。
前两次吉哈德浪潮是由社会精英出身的领袖和主要出身下层中产阶级的群众(大学毕业生居多)组成的,而伊斯兰国的骨干则在农村,他们缺乏宗教和智识方面的素养。
社会的衰退
伊斯兰国和穷苦的农村逊尼派社群打成一片,并在那里建立了它潜在的社会基础。
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地区,是滋生争斗的社会温床——数十年的社会衰退和国家腐败使这里的年轻人对当局深感幻灭。

伊斯兰国就是以这些区域,比如说,最贫穷的摩苏尔和拉卡地区为目标的,摩苏尔和拉卡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控制的人口最多的两个城市,他们在这里招募士兵和警察,给他们提供武器,支付薪水,并通过建立巡逻队而赋予他们权力。
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急速的军事扩张源于其恐吓、震慑敌人,和用经济上的激励和庇护与特权网络(比如说,保护被禁止的运输活动,和在叙利亚东部石油贸易和走私的利润上给他们分肥)来拉拢当地贫穷的逊尼派群众的能力。
从许多方面来说,当前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四处蔓延的逊尼与什叶之争,更是一场社会-经济战争。
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核心,是农村与城市穷人的起义。
伊斯兰国的力量之一,就在于其针对这部分弱者,和操纵其对国家体制未能满足其公民一些最基本需求的愤怒的能力。
阿拉伯世界及阿拉伯世界以外的外籍战士的涌入,也证明了伊斯兰国的反叙事(或者说对抗叙事)的力量,及其把士兵变成准备好为组织献出生命的忠诚的杀戮机器的能力。
伊斯兰国老练的外展活动,通过把该组织展示为一个有能力取得胜利、赢得救赎的强大的先锋运动,而吸引了全世界不满于现状的逊尼派青年。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观和一个政治计划——复兴已经失去的哈里发国。
伊斯兰国坚持不加限制的全面战争原则。它蔑视仲裁或妥协,甚至对(同为)逊尼派伊斯兰主义(阵营)的竞争对手也如此。
和基地组织不一样,基地组织只依赖神学来给它的行动正名,却没有看到发布一个神学或宗教宣言的需要:伊斯兰国就发布了这样的宣言,因为毕竟,它已经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哈里发国并控制了从叙利亚到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其领土和英国一样大,它统辖的人民多达五百万人。
绝望感
然而,伊斯兰国要比巴格达迪想让我们相信的脆弱得多。
高层吉哈德主义的宣扬者、和主流伊斯兰主义组织都不接受他的号召,而伊斯兰学者——包括最著名的塞莱菲人士——也谴责他的宣言,认为他的宣言无力且无效。
如果伊斯兰国要一直赢下去,它就不能摆脱其观念的贫乏,以及来自穆斯林公共舆论的广泛的反对:伊斯兰国许诺了乌托邦,它只有通过胜利才能实现那个乌托邦。
伊斯兰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一旦它前进的步伐遭到限制,其连贯自洽的意识形态的匮乏,将加速其社会的衰亡。

在我和伊拉克部落领袖的谈话中,许多人承认,他们的儿子加入伊斯兰国的车队不是因为伊斯兰国的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他们有吸引力,而是因为他们把伊斯兰国当作反抗巴格达的什叶派中央政权及其在该区域的庇护者——伊朗——的手段。
伊斯兰国迅速占领所谓“逊尼派三角”的大部分地区这一事实,及其惯用的自杀性爆炸——特别是针对什叶派的——和反美修辞,对那些感到自己家国被美国(在伊朗的支持下)羞辱和殖民的逊尼派青年来说很有吸引力。
那么,成千上万名逊尼派伊拉克人在伊斯兰国的旗下战斗,却不信奉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的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也就不奇怪了。
也许,伊斯兰国以被剥夺权利的逊尼派社群为目标(这一举动)的最令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它操纵了在此区域广泛流传、并在2010年至2012年间触发阿拉伯之春的那种深刻的绝望、无望感。
在中东,百姓一直在为他们的权利、自由和自决而斗争,而几十年来,这些斗争并不必然就会使用暴力。
在伊斯兰国热切宣传这样的信念——即,野蛮是比公民抵抗更有效的,反对当地统治者、挫败外国列强的、帝国主义奸计的动员工具——的时候,它不过是在重复以往这个区域的独裁者惯用的那套说辞罢了,这套说辞以本真性的名义为专制披上合法的外衣。
通过把自己描述为当前那个破碎的、腐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替代选项,伊斯兰国也就夺走了人民的能动性。
通过否认公民运动引发变革的力量和核心作用,像伊斯兰国和努斯拉阵线那样的组织使用的,其实是一套把抵抗等同于歧视和残酷暴力的叙事。
持久的遗产
在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国在这个区域最有害的持续影响之一,是它取消或抹杀以公民为动力的战略的战略,而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区域的变革,本是可以通过公民的运动来实现的。
相应地,削弱伊斯兰国的关键也就在于,与它已经拉拢的逊尼派社群密切合作,这就要求我们采取一个自下而上的进路,这个进路要求大量的物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入。
削弱伊斯兰国的最有效的手段,是通过赢取民心来瓦解其社会基础(这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任务),以及,解决给伊斯兰国以动机、资源和避难所的叙利亚冲突。
确实,要使中东摆脱伊斯兰国的控制,我们并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解决方案,因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是该区域国家政权解体、社会经济形势惨淡和教派冲突蔓延的集中表现。
说到底,伊斯兰国是该区域的积怨,意识形态与社会的极端分化,及其在崛起的十年中所进行的社会动员的产物。
法瓦兹·盖尔盖斯(Fawaz A. Gerges)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与中东政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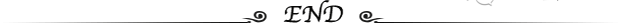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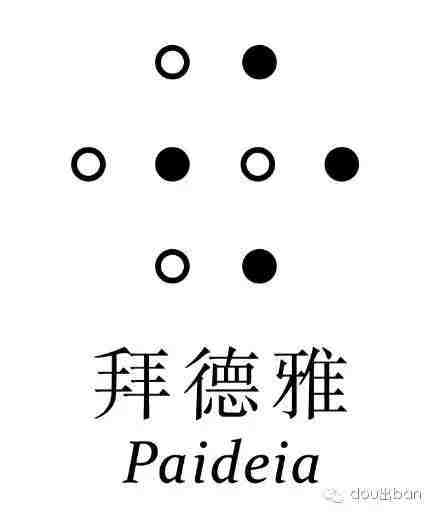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诚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品○●○●
“导读”系列衍生的一个图书品牌



最新评论
推荐文章
作者最新文章
你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Copyright Disclaimer: The copyright of contents (including texts, images, videos and audios) posted above belong to the User who shared or the third-party website which the User shared from. If you found your copyright have been infringed, please send a DMCA takedown notice to [email protected]. For more detail of the source, please click on the button "Read Original Post" below. For other communications, please send to [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用户推荐收藏至CareerEngine平台,其内容(含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及知识版权均属用户或用户转发自的第三方网站,如涉嫌侵权,请通知[email protected]进行信息删除。如需查看信息来源,请点击“查看原文”。如需洽谈其它事宜,请联系[email protected]。